诺兰谈奥本海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后被黑暗攫住
“我希望电影在开放系统中推进下去——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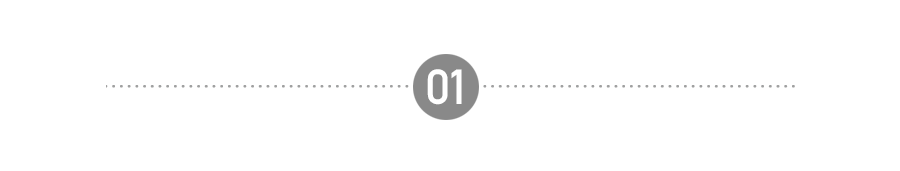
电影《奥本海默》的剧本,导演、编剧克里斯托弗·诺兰使用第一人称来写作。制片人、演员们读过后感到惊讶,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剧本。“它给了你一个非常主观的内心体验。”片中演员马特·达蒙说。
电影改编自获普利策传记文学奖的作品《美国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成功与悲剧》,作家凯·伯德和历史学家马丁·J.舍温历时25年,通过大量访谈、信件、日记,以及美国的解密档案和联邦调查局文件,以极细腻的具颗粒感的笔触描摹了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一生。
1904年,奥本海默出生于富裕的纽约犹太家庭,聪慧、敏感,热衷自由主义。即使后来他选择理论物理作为毕生研究方向,也始终对文学、哲学和天文学抱有极大兴趣。他读美国作家E·E·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卡明斯认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自由。”他在犹太社团学校习得的行为准则成了他的人生信条以及对弟弟的教诲——人必须对他所选择的生活和命运负责。
奥本海默对天文学的兴趣,引导他和学生哈特兰·施耐德合作完成论文《论持续的引力收缩》,于1939年9月1日发表。这篇“奇妙又怪诞”、在当时被认为是“数学上的狂想”的论文其实预测了黑洞的存在,“开启了通往21世纪物理学的大门”。
但论文发表当天,被开启的是另一扇门——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开始。
物理学家们四处寻求庇护,卷入军备竞赛。由美国主导、致力于研发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开始后,奥本海默成了实验室主任,统筹科学家们在新泽西州的沙漠深处为秘密研发效力。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二战结束,奥本海默顺势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
狂欢与死亡同时来临,他意识到作为几乎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原子弹的使用与否已经失控。奥本海默被内心的道德感折磨,他发表演讲反对核扩散和更具威胁的氢弹,但战后兴起的反共情绪和麦卡锡主义则从外部将他推入绝境。在一场历时四个星期的闭门听证会上,原子能委员会捕风捉影地将他和共产主义挂钩,试图将其污名化。最终奥本海默被撤回安全许可——这意味着他无法再接触政府的核弹研究机密——直到1967年他去世也没有恢复。
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的叙述中有种宿命般的悲剧语调,科学与政治相互依存、背弃,个人对世界事务的道德责任似乎不值一提,而围绕奥本海默的故事已经完全超出了他本身。
传记于2004年底完书,结尾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准备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以表彰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并为其恢复名誉。计划还未成行,肯尼迪遇刺。直到2022年12月16日,也就是8个月前,拜登政府才推翻了1954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平反迟到了将近60年。
诺兰把传记读了好几遍,不做笔记,然后合上书,“记忆和潜意识会告诉我哪些事情让我难以忘怀,如果没有出现在我最初记忆里,那我相信它也不需要出现在电影里。”2023年8月25日,他即将结束中国之行的这个上午,我在酒店会议室见到了他。和往常一样,他穿着西装外套,手上的保温杯没盖盖子,冒着热气。在前一天的映后活动中,他讲到对他来说写剧本比拍电影更难。但从1996年拍摄第一部长片到现在,除了《失眠症》(2002),诺兰每次都参与剧本创作。为了“触摸到奥本海默头脑中的声音”,他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根据记忆搭建大纲。
在一次和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谈话中,诺兰曾提到自己青春期时的恐惧。作为1970年出生于伦敦的英国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北伦敦经历过核裁军运动。13岁时,他和朋友们都相信有一天自己会死于核爆炸。但创作《奥本海默》期间的大量案头工作,让他意识到一种新的恐惧,越深入那些历史和研究,越会不自觉地把核武器正常化,把它带来的杀伤和在政治博弈中扮演的角色正常化。
诺兰将之视为一种警示,像片中演员小罗伯特·唐尼所说,“就在我们开始拍摄时发生的一系列全球事件为这部电影赋予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可以涵盖各种主题。”
2023年7月21日开始,《奥本海默》在全球陆续上映。一个月后,票房接近8亿美元;截至发稿前,位列2023年全球票房榜第四。
诺兰有一套成熟的创作法则。
因为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经常往返于英美,在6个小时时差之间切换。他是左撇子,会从后往前翻阅菜单、书籍。时间、叙事的多维和跳跃既是诺兰的生活经验,也一再被置入他的电影框架中,构成螺旋式上升的结构。他在短片《蚁蛉》(1997)中使用环状结构,密闭房间里不断拍死的蚁蛉其实是微缩的自己。《追随》(1999)三线并行,从故事开头、中途和结尾同时切入。《记忆碎片》(2000)将此推向极致,诺兰采用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患有短时失忆的主角兰纳被警察和酒保利用而杀人。影片结构锋利、剔透,他把故事拦腰斩断,一半以黑白拍摄,主观视角;顺叙,一半以彩色拍摄,客观视角,倒叙,再剪碎为片段交错重组,最终在中点汇合。
《记忆碎片》是当年独立电影的票房黑马,之后诺兰的导演生涯相当顺遂,《失眠症》中他和两位奥斯卡影帝阿尔·帕西诺、罗宾·威廉姆斯合作,在好莱坞制片厂中赢得声誉。接着改编《蝙蝠侠》三部曲,为超级英雄故事注入严肃内核。这其中体现出对人物道德困境的喜好,就像对记忆、梦境、物理的喜好一样延续至今,以现实为边界进行奇想。使他声名大噪的《盗梦空间》(2010)和《星际穿越》(2014),前者是意识层面的抢劫片,后者是五维空间的家庭赞美诗。
结构、道德困境、奇想增加了电影趣味,使它经得起反复观看,诺兰收获了大批粉丝。但有时也会成为观众的观影障碍,有评论认为他精于类型片的打磨,但角色缺乏由内而发的真实情感。
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电影制作习惯。
诺兰会在影片开拍前就见作曲家,讨论整部电影的配乐,配乐是叙事线。他在片场只用一台摄影机拍摄,使用胶片,20分钟一卷的胶片一转动,就开始烧钱,所有人必须专注。除此之外,诺兰非常推崇实景摄制。《星际穿越》筹备时,他们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的山脉间种植了500英亩的玉米,又随剧情需要付之一炬。《信条》(2020)中飞机被撞毁的桥段,由一架报废的波音747完成。
到了《奥本海默》,像往常一样,诺兰不喜欢使用CG特效,又要制造原子弹爆炸的场面,大家略带调侃地猜测:诺兰真的炸了原子弹吗?还好不是。视效总监安德鲁·杰克逊最终通过微缩模型和大型爆炸完成了“三位一体”实验(人类史上首次核试验的代号)场面。爆炸那天,“气氛非常紧张,这种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夜晚和清晨的情景,也影响了演员们演绎这个场景的方式。”诺兰说。
无论如何,诺兰是当下少数能够兼顾票房和口碑的导演,入围5次奥斯卡金像奖、5次英国电影学院奖和6次金球奖。他的影迷们乐于把他视作“新千年的库布里克”,斯皮尔伯格则称他为“好莱坞最后的电影作者”。
在《诺兰变奏曲》中,诺兰讲过一件事,体现了他对自己所做之事的认知。
几年前我跟一个制片人共进午餐,他是非常成功的制片人,我们没有合作过,他对我的工作方式很好奇。聊到一半时,我说:“我每次拍一部新片,都必须相信自己正在制作有史以来最棒的电影。”这让他非常吃惊,他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思考。而他的反应也让我很震惊,因为拍电影很困难,虽然我不会说这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我从未尝试过挖煤矿——但电影会消耗一切,你的家庭生活、所有一切都得投入电影,长达数年。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拍电影的人竟然不努力拍出有史以来最棒的片。为什么不这样努力?即便它不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电影,你也必须相信有这个可能。你必须全心投入,当我的电影也这样令人全心投入,就让我非常开心——开心极了。我觉得自己成功地用我的电影把人包裹起来,正如同我也努力把自己包裹起来一样。
一些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无法回答——对话诺兰
南方人物周刊:你大概花了多久来写作《奥本海默》的剧本呢?
诺兰: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写笔记、思考和研究,但实际写作很快,大概花了六个月。因为我是根据一本花了 25 年才写成的书进行写作的,所以,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的书里有关于奥本海默的一切,我额外做过一些研究,但确实是那本书给了我信心,也使这部电影能被拍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当你使用第一人称来写作,通过奥本海默的眼睛来看那段历史和那些人物,在哪些地方你与他产生过强烈共鸣呢?
诺兰:我必须找到与这个角色的契合点。他有远超常人的智识,思考着我们无法从字面理解的概念。所以,我的抓手就在于,当他成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director)时,他和我一样是个“导演”(director),必须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期在特定的时间内实现特定的目标。这让我产生了情感共鸣。
因此,我试着从情感而非智力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天才。他年轻时在剑桥试图将量子世界可视化,那时候量子力学正在彻底改变物理学,我试图把它表现为一种神奇的洞察力和魔法,是他的感觉,而不是思考。当时,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能力有所感知,却无法将之表达出来,也无法转化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这又是一种熟悉的、我们都曾经历过的青春期感受,也让我产生了共鸣。
后来,随着他的故事产生越来越严肃的、全球性的影响,他陷入道德困境。显而易见,我们都能体会到他所面临的困难,那么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希望电影在开放系统中推进下去——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奥本海默的了解其实由来已久,随着成长经验的累积以及电影项目的进行,你对这个人物的看法是如何逐渐演变的?
诺兰:是的,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奥本海默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它与二战中的原子弹紧密相连。但还有另一种联想,一种黑暗的联想,很多人并不完全了解。我当然也不完全了解。随着我越来越深入他的故事,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我之前在《信条》中提到的,奥本海默和他“曼哈顿计划”中的同事在进行“三位一体”实验时,无法完全消除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当他们触发该装置时,会引发链式反应,引燃大气层并且毁灭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令人恐惧的理论可能性。同样震撼、令人恐惧的是,他按下了按钮,替全人类做出了决定。
然后,到了战后,我隐约知道他遭遇了不测,回顾历史才知道这与 20 世纪的美国历史、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的反共热潮息息相关。他以一种臭名昭著的方式被卷入其中,留下了模棱两可的遗产和声誉。
在小说中,我就一直被这类人物吸引。他不是一个明确的英雄或反派,他两者兼具。他包罗万象,同时非常人性化。
南方人物周刊:很有意思,我记得在造型上你们既借鉴过大卫·鲍伊,又在海报和片中几处呈现了他像死神一样的一面,是吗?
诺兰:奥本海默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其实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就像大卫·鲍伊这样的明星一样。我给基里安(奥本海默的扮演者)看过一张鲍伊的照片,照片上的鲍伊穿着巨大的宽松长裤,那是他风头正劲的时候。我还找到一张奥本海默的照片,他和鲍伊一模一样。奥本海默成功地将自己符号化了,以至于在战后,有一本杂志的封面上只有他的帽子和烟斗,但每个美国人都知道那是谁。我认为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试图在影片中展现这一点。他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展现自己,因为他觉得这给了他力量,带来了关注和可信度,给了他话语权,他觉得他可以利用这些做点好事。
我希望基里安在拍摄时也能始终有这种意识。有趣的是,尽管基里安是个出色的演员,但他不是一个戏剧化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展示自己,他很出色,但我不认为他能立刻体会到角色的那一面,需要大量的对话和思考,才能意识到奥本海默是多么具有自我创造力和自我意识。
南方人物周刊:既然说到了基里安,为什么选择他作为奥本海默的饰演者,以及为什么选择小罗伯特·唐尼来饰演施特劳斯(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后组织秘密听证会指控奥本海默为苏联间谍)呢?
诺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奥本海默深邃凝视的眼神,而基里安的蓝眼睛,比你能说出的任何演员都更有这种气质。小罗伯特·唐尼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电影明星之一,我们这些好莱坞人一直都知道,他的才华令人难以置信。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做一些沉浸其中甚至有点迷失自我的事情了,这真的很有趣。
南方人物周刊:这部电影里有大量由IMAX摄影机拍摄的特写镜头,甚至为此托柯达公司定制了一批黑白胶片,一种影史上从未有过的胶片。这样高规格的格式以往大都用来拍摄风景,为什么你们会将它用于特写?
诺兰:没错,我和我的摄影指导霍伊特·范·霍伊特玛在拍摄这部电影前就知道,它非常适合新墨西哥州的地貌,在那里我们能拍摄风暴和“三位一体”测试。但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IMAX能为“艺术大师的脑袋”这一概念做些什么,能为人类的脸做些什么。IMAX格式的有趣之处在于,在所有的大银幕电影格式中,它实际上是最接近于人像的一种,因为它是1.37:1的画幅(早期的主流电影画幅,适合特写,一度被作为电影制作的统一比例,也被称为“学院画幅”),非常适合拍摄脸部。因此,在我的其他电影中,我们曾使用它来拍摄富有表现力的镜头和脸部,但我们从未像这部电影一样,尝试使用它来贴近角色,与角色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发现其实这种格式非常适合,图像的清晰度和锐利度可以让银幕消失,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在角色身边。
南方人物周刊:和你以前的电影很不同的一点是,《奥本海默》的戏剧冲突都发生在人物内心及人物关系之间,这次和以往创作、执导的经验有什么不同吗?
诺兰:我认为,要让观众获得同样程度的参与感和兴奋感,但不是靠汽车追逐和飞机坠毁,而是文字、人际冲突,是一件需要扩大电影制作规模、提高信念感的事。我们希望影片给人以大片或动作片的感觉。因此,我们尽量不去想太多,我也尽量不去想太多,只是相信故事。我相信奥本海默的故事是我见过的最戏剧化的故事。
另一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是,当我在写剧本时,我采取的方法是,影片中间的“曼哈顿计划”是按照以语言为要素的类型片来构建的,也就是抢劫片。我们把一队人聚集在一起,交代目标,看能否实现。在影片第三幕,我的关注点转向另一种类型片,语言同样是重要因素,那就是律政剧。在那里,有证人在作证,他们说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所有主角的命运。我采取了这些方法,但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相信戏剧故事的过程。
南方人物周刊:我想问一个细节的问题,刚才你提到那个毁灭世界的理论可能性,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得知的吗?
诺兰:老实说,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了。几年前,我把它写进《信条》,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有用,非常贴近科幻小说的概念。但其实奥本海默对我来说,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意识的边缘。奥本海默生前非常有名,但现在知名度并不高,这部电影把他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也是我后来发现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那么重新理解这样一个意识边缘的人物,会唤起你青少年时期关于核武器威胁的记忆以及更多情绪吗?和你以往多少有种乐观在其中的电影不一样,它显得黑暗和虚无。
诺兰:是的,确实如此。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试图以一种不压抑、引人入胜、生动活泼的方式,让人们了解或理解这个复杂人物的故事,他是故事的主人公,你会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但我相信,最终,我们都无法摆脱他带来的黑暗、他对世界的改变。我并没有强调这种黑暗,而是让它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故事中。对我来说,沉浸在冒险和胜利的喜悦中,然后被黑暗攫住,这更有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在大概两个月前的采访中,你曾提到《奥本海默》的结尾和《盗梦空间》的结尾之间有种有趣的关系可作探讨,愿意多谈谈吗?
诺兰:挺有意思的。我认为两个结局都给观众留下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两部影片中,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尝试,即在整部影片中都保持故事情节,沉浸在影片的世界中,然后在结尾时,你会被拉出来,提醒自己某种现实的存在。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让观众回到现实的设置,是想对当下现实世界中的观众说些什么吗?
诺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制作一部电影时,我不会试图传达某种特定的信息。我认为试图让电影说教,效果并不好。它们会变成宣传片,人们往往拒绝接受,觉得自己被操纵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表达戏剧性情境、矛盾感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
作为导演,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提出真正有趣的问题,但不是假装我有答案,因为我没有。我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无法回答。当然,如果人们在看完这部电影后,对核武器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了更多关注和兴趣,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
南方人物周刊:算上五年前的《敦刻尔克》,你已经拍了两部回到历史的电影,是否意味着视角的转变?
诺兰:不,我不这么想。我只是对最戏剧化的故事感兴趣,有时是真实的生活,就像《敦刻尔克》,有时像《信条》和《盗梦空间》。我喜欢在每部电影里挑战自己。当然,《敦刻尔克》对我来说无疑是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我从未以真实历史为内容来拍摄,特别是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故事,是一个神话,这样做非常冒险、困难。但它成功了,人们喜欢它,这可能是我能够接拍《奥本海默》的原因。
南方人物周刊:我连续两天在电影院看《奥本海默》,意识到它的魅力是在电影院才能被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但因为新冠疫情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进电影院看电影,那段时间你是如何度过的,是否会对电影这件事产生新的思考?
诺兰:我住在洛杉矶,电影院关闭的时间很长,长达一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这很有趣,非常有趣,使我反思电影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
对我而言,我非常坚定地相信戏剧的必要性和力量,相信戏剧体验和公共体验。我意识到,流媒体和其他形式根本无法取代戏剧体验,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媒介。我非常想念它。所以,现在看到人们重返影院真是太好了,这对我所热爱的媒介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年轻人来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鼓舞,也非常令人兴奋。
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你对观影前的观众有什么想说的吗?
诺兰:我认为《奥本海默》的理想观众是对历史和科学一无所知的人。这才是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真正目的。因为事实是,即使在美国,人们对这段历史也只是略知一二。即使是那些自以为知道很多的人,当你真正了解这段历史时,仍会大吃一惊。这不是一部传记片,而是一部戏剧性的故事片,所以我们希望让观众参与进来,给他们带来惊喜和兴奋,我认为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